威廉·福克納《士兵的報酬》:一位青年作家的惶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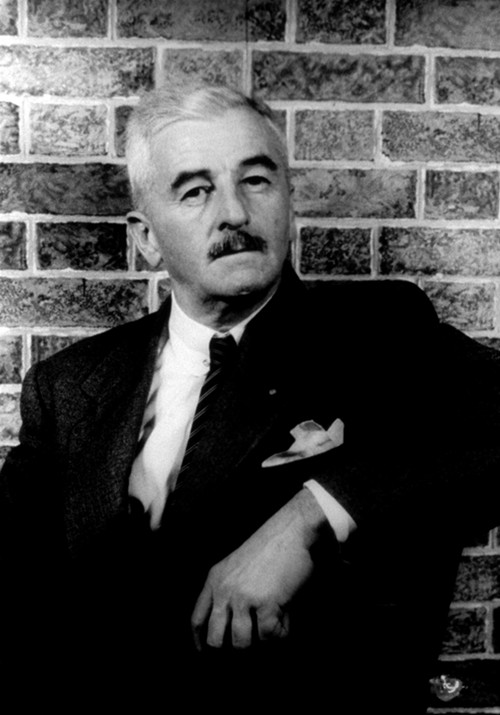
在福克納的處女作《士兵的報酬》中,重傷士兵唐納德·馬洪回到家鄉,迎接他的卻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新世界。對于他,以及他所象征的那一代渴望在戰爭中解決問題、實現自我的年輕人而言,這個新世界并不是為他們準備的。他們用四年時間耗盡一生,苦熬著換來一份并不牢靠的和平,盡管如此,轉瞬間他們還是被這個由新道德宰制的世界拋棄了。看起來,以如此方式實現自我的成本顯然是太大了。但此刻,作為青年作家的福克納還沒有能力去徹底地思考這個問題。他只是盡可能忠誠地去描述那心中之眼對時代的諦觀。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關注的正是戰爭之后這個他們曾為之爭取和平反過來又傷害他們的世界。這些人不是一個穩定的作家群,他們短暫地置身其中,繼而分道揚鑣。然而在這批作家最初的作品中還是能夠察覺到一些共相,譬如主人公不僅在肉體上遭受到可怕的重創,精神上同樣未能幸免于難。肉體的損害發生于戰爭之中,精神的沉淪則落實在戰爭之后。甚至可以這么說,相較于道德維系、倫理觀念與人生理想的過早失落,那在肉體上失掉的尋歡作樂的可能,不過是精神的一種隱喻和暗示而已。
《太陽照常升起》與《士兵的報酬》同年出版,小說中的杰克·巴恩斯也是受傷的一員,但重新將巴恩斯接納的新世界,卻是一個名叫勃萊特的女人處處留情、因此需要他時時救場的世界。不過,此種心態又無法被當代的怨恨解釋學涵蓋。當他在出租車中說出這樣的話時——“這么想想不也很好嗎?”——“迷惘的一代”只能說是天真的、感傷的以及惶惑的。福克納的第一部小說亦是如此,戰爭的摧殘已經使得馬洪有口而不能言,有目而不能睹。他是一個正在死亡的神靈,安坐在椅子上,用簡單的詞語回答人們的疑惑和請求,用漸漸失去的視力注視著這個由他創造卻倍感陌生的世間:
對唐納德·馬洪來說,時間正慢慢離他而去,不過這世上已經沒有讓他牽掛的東西,失去也無所謂,他望著窗外綠色的、紋絲不動的樹葉:一片紋絲不動的模糊。
與這尊沉默或正在死去的神形成反差的,是周邊人的態度與反應(福克納在1954年的《寓言》中給出了他對此的看法:“對于這些拯救了世界的士兵來說,他們所拯救的世界不配讓他們付出如此代價”),包括馬洪的父親、未婚妻以及馬洪在退伍列車上偶然結識的朋友。德國觀念論者對現實主義的擁護是很有道理的:在大多數人那里可能連現實主義這一層面都沒有達到。老馬洪便是這樣的人,作為鄉間一位虔敬的神父,他對于自己兒子在戰場上的遭遇,只能抱著逃無可逃的鴕鳥心態,不時從他人那里討一些安慰寬心。
至于馬洪的未婚妻塞西莉小姐,則與《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勃萊特夫人如出一轍,其態度之多變詭異可發一噱。當塞西莉小姐最初聽聞馬洪即將歸來時,內心所想的是,“現在我又是個訂過婚的人啦”,“她沾沾自喜,等喬治聽到這個消息,他的臉上該有多么驚訝的表情,她越想越樂不可支……她凝視著他,然后迅速將視線轉移到一旁。真可笑,居然是因為一個局外人讓她重新燃起對唐納德的渴望,期盼他的歸來。她木然地點點頭,心頭一陣痛楚,悵然所失”。緊接著,她便因為戰爭在馬洪臉上留下的可怕傷口而認為自己“還沒做好結婚的準備”,并且順理成章地發展到下一階段:“‘不,我跟他結束了,聽好啦。他當著她的面讓我難堪。’她的手終于得到解放,她快步向落地窗方向走去……‘我已經忘了他。他不再需要我了。’”事情至此并沒有告一段落,此后又接連出現兩個短暫的高潮,其一是塞西莉小姐突然宣布要和行將就木的馬洪結婚,其二是同自己的情人喬治·法爾在亞特蘭大迅速舉辦了婚禮。這樣的女性形象還將在《圣殿》中以譚波兒的名字出現。
在這些人里,馬洪在列車上偶然結識的朋友喬·吉利根與瑪格麗特則與他父親和未婚妻的態度形成了二次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吉利根這個人物形象。小說開篇時,他是那個在火車上假借酒意尋釁鬧事的——雖然他自始至終都很清醒,他懂得將自己灌醉以此避免與這個戰后的世界直接打交道——“亞普漢克”,然而隨著吉利根同瑪格麗特在美國南方小鎮悉心照顧馬洪,吉利根的善良本性逐漸顯露出來。誠如他在小說即將結束時對瑪格麗特的那番告白:“雖然我們的看法不同,世事的變化卻一如既往。我猜這是人類舊有的本性,像做批發生意,讓我們對一切不再驚訝,更不用擔心我們會迎來怎樣的人生,是否如愿以償。”戰后的經歷對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教育,即不必再借助醉生夢死來掩飾不安。故事在馬洪下葬之后沒有戛然而止,或許也有這方面的考量:福克納需要努力寫出一個新人形象:那個“亞普漢克”已經讓渡成為一個有擔當的男人喬·吉利根。
戰爭曾是馬洪和巴恩斯這批年輕人的啟蒙課堂。他們從未理解戰爭為何物,是炮火激發了他們年輕的心,于是他們便懵懵懂懂地、懷揣著渴望借此擺脫自身不成熟狀態的愿望投身到可怕的風暴眼中——也許即使在南北戰爭期間青年人也是如此,誠如《押沙龍,押沙龍》中亨利對邦的勸導:“可是你必須等待!你必須給我時間!說不定戰爭會解決這個問題,無需我們操心。”彼得·艾奇格爾于《小說中的美國士兵》中評價福克納的這部處女作說:“它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象征,它還深刻地揭示了美國理想主義者在殘酷恐怖的戰爭面前精神上受到了何等巨大的創傷,他們為了認識這場戰爭所做的努力使他們的理解能力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作為社會個體——被摧毀了。”事情的真相恐怕并沒有他描述得這樣樂觀。戰爭結束后,作為個體的士兵確實被摧毀了,這沒錯,但他們的理解能力并沒有隨著戰爭的遽然結束而飛升到一個新水平(后一點只有在自我啟蒙的事業中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他們在日后才能明白的事情:教育與生活的同步性)。因為所謂摧毀,只能是肉體的創傷連同精神的幻滅。《太陽照常升起》與《士兵的報酬》寫的都是戰后青年人的心靈之死:
這樣處理看來可以解決問題了。就是這樣。送一個女人跟一個男人出走。把她介紹給另一個男人,讓她陪他出走。現在又要去把她接回來。而且在電報上寫上“愛你的”。事實就是這樣。我進屋吃中飯。
——《太陽照常升起》
他們歡迎他的加入,跟他寒暄,他們受邀參加舞會,卻不太清楚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也不知道主人邀請他們出于何種目的;總之,這些土生土長的鄉村男孩似乎闖入與淳樸家園風格迥異的繁華都市,一時手足無措。他們覺得自己是鄉下的粗人:發現傳統的品行一夜之間變得過時,這實在讓人費解……戰爭曾是人們說不盡的談資,戰場的洗禮也將他們從少年成長為男人;但如今人們似乎已經找到其他飲料解渴,而他們還不習慣。
——《士兵的報酬》
至于這一切為何能在瞬間完成,則需要我們追溯到戰前與戰后時代精神的轉變之上:這是一種名為現代主義的新道德對長久盤桓在美國上空的維多利亞式傳統道德的猛烈沖擊。事實上,20世紀初的美國已經沒有太多可供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堅持其信念的土壤,亦即去堅持一種人格同一性的信條,不過是福克納家鄉的封閉性依然為此制造出了一種忠誠于傳統文化的幻覺。兩種道德的沖突,準確地說是思想態度的抵牾,而在思想態度的背后則是一種形而上學假設的對立。現代主義拒絕承認人格的同一,這在此刻依舊是可能的,因此每個人的自我認同與其說是接受一種遺贈式的傳承,毋寧說是需要個人不斷且主動地去為自身制造面具。對現代主義而言,重要的是感受性的體驗,而非理解性的知識,進而在充分接近無意識的層面抵達本真意義上的真實。現代主義者毫無疑問是反叛的,但他們的反叛是實用性的,是為了重建一個包羅生活萬象、沒有等級宰制的日常秩序。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尤其是像福克納這樣的南方之子。如我們所知,自從南北戰爭結束以后,美國的南方就成了舊神話的王國,而舊神話是南方賴以生存的自尊。
置身于這種可怕張力之間的藝術探索,并沒有毀滅一個藝術家,相反,張力本身塑造了福克納——借用丹尼爾·J.辛格的說法——福克納漸漸學會了“一種傾聽內心發出的聲音而后盡可能忠實地將其復制書寫下來的寫作方式”。這個時候,作為作家的福克納就能夠處理張力的困境:通過深入到每個人物的意識之內,從而將張力移置到故事層面,借此保障了錯綜復雜的意識與困境同在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是多重意識的真實性,它以殺死作者的聲音,或逼迫其退隱到文本幕布之后為前提。我們不妨將福克納的所有創作皆視為內在于這種困境的個人實踐活動,而在其藝術巔峰時期,每一部杰作的產生都有賴于對這兩種道德游刃有余的處理。
因此,如果說在1926年的福克納筆下,展現的是兩種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之后的道德廢墟,那不過是因為他還沒能意識到自身依舊在兩種思想態度之間搖擺不定,也還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寫作方式去升華惶惑的根源所在。此刻的福克納只能帶著不確定性去描述諸種場景,他無法準確地認識它們。《士兵的報酬》便是如此,它既是福克納的處女作,也是其創作的源頭,后者指的是他能夠通過寫作來提出問題,而問題總是延異的。這是一個年輕作家面對那種名為現代主義的新世界的大惑不解。他像馬洪一樣沉默和惶惑,熱忱地等待著三年后的自己來回答此刻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