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斯《芬尼根守靈夜》中國字謎的破譯之旅
2019年5月,長篇小說《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1939,以下簡稱《守靈夜》)出版八十周年,我們尚未超出喬伊斯“要讓評論家們忙上三百年”的預言。《守靈夜》極致的風格實驗,讓人懷疑這是一部關于睡眠或夢的瘋狂之作。喬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Stanislaus Joyce)、贊助人韋弗小姐(Harriet Weaver)、好友龐德(Ezra Pound)等一貫忠誠的支持者均表示不解,擔心喬伊斯在浪費才華。早期學者試圖就其可解部分構建一個連貫的故事,如著名的《〈守靈夜〉的萬能鑰匙》(Joseph Campbell and Henry Robinson, The Skeleton Key to FinnegansWake, 1944),其實是避重就輕,不免牽強。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喬伊斯的大量筆記揭示,小說中的大部分語匯固然是作者自編的,卻不是瞎編的;學界順藤摸瓜,回溯了一些語匯從《守靈夜》到喬伊斯的筆記,再到他所讀書刊的“變形”過程。盡管如此,《守靈夜》至今仍是世界文學中最難懂的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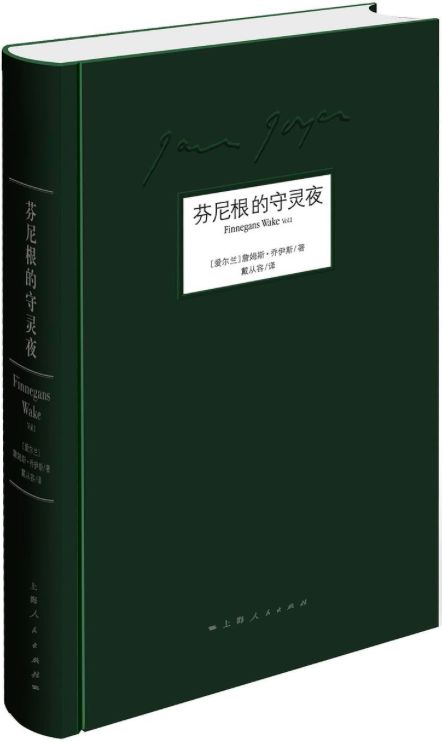
《芬尼根守靈夜》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部“天書”實在是繞不開的。喬伊斯不懂漢語,小說中亦無漢字,但他化用或編造了大量羅馬字母轉寫的中文,指涉中國的方方面面:上至伏羲孔孟,下至辛亥革命、西安事變,以愛爾蘭都柏林的利菲河為母題之一的《守靈夜》也流淌著長江、黃河、黃浦江,小說對姜、絲、茶等中國物產的指涉、對以中國為題材的當代西方流行戲劇的引用,既攜帶又超出“東方情調”。在某種意義上,《守靈夜》是一部宇宙史,喬伊斯所用的全球八十多種語言、方言、人造語正涵此意,而與西方語言完全異質的漢語,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為這座巴別塔添磚加瓦。
八十年來,喬學界的中文破譯成果集中體現(xiàn)于麥克休一版再版的專著《〈守靈夜〉注解》(Roland McHugh,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1980, 1991, 2006, 2016)。麥克休應該不懂中文,他在致謝中提到懷特的未刊稿《〈守靈夜〉的中國詞語與典故》(H. M. Hope Wright, “Chinese Words and Allusions in Finnegans Wake”)。近日,都柏林的喬學家迪恩(Vincent Deane)向老友麥克休借得這份四十多年前的打字稿,筆者遂有幸通過迪恩讀到其掃描件。
漢學家的推測
關于懷特的信息很少,從其文章看,她大約是居住在倫敦的一位中國文化研究者。《〈守靈夜〉的中國詞語與典故》應寫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29頁導言和180頁詞匯表組成。詞匯表列出《守靈夜》中的詞句及其頁碼、行數(幾乎所有版本的每頁排版都一樣),下面是懷特的注釋:可能用了什么中文字、解釋和出處。麥克休從中摘出最可信的條目,精簡為一份8頁的打字稿,對照可知,這成為《〈守靈夜〉注解》的中文注釋的主體。
作為破譯《守靈夜》中文的試水者,懷特的成果有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第一,她對破解中文的困難有清晰的認識。導言介紹了漢語的構成,特別是同音字比例高的特點。口頭和書面漢語都好區(qū)分,但經羅馬字母轉寫后,就很難確定是哪個字。況且,不可能近似中文音節(jié)的就都是中文,如 an、ma、man也是英語或其他語言中的詞。更麻煩的是,轉寫體系不一,故拉丁化的音節(jié)只是接近中文讀音而不夠準確。喬伊斯至少用了英語和法語兩種轉寫方案,如chang在英語即威妥瑪式(Wade-Giles)拼寫中,讀作現(xiàn)代漢語拼音zhang,若是法語則讀作漢語拼音shang,所對應的字隨之不同。此外,拼寫錯誤常見,更添混淆,一如文字游戲兼主題之一——“混淆”(confusion)與“儒家的”(Confucian)難舍難分。對此,懷特在本導言及另一篇論文中表示,與其依賴漢英字典,她更傾向以《守靈夜》文本中其他地方的指涉來幫助判斷。第二,她對中國語言、文化、歷史相當熟悉,讀了不少經典。她指出喬伊斯用了一些中國經書之名,而非其內容。根據自身的閱讀經驗、某些措辭的相似,她推測喬伊斯讀過《漢語的音與符》(Bernhard 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等書。chanching一詞可看作change+ching,懷特推測,喬伊斯用了《易經》的理雅格(James Legge)譯本,因為《易經》的一種音譯為I-ching,理雅格意譯為Book of Changes。另外她認為,《守靈夜》化用了涉及中國題材的流行歌曲、歌劇。第三,她知悉喬學動態(tài)。她留意到艾爾曼《喬伊斯傳》(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1959)中的一個細節(jié),1927年3月2日,喬伊斯在信中提到一位中國學生回復了他關于中國字的問題,可惜清單不存。在確定具體漢字的問題上,她遵循喬學界已發(fā)現(xiàn)的一些原則,如意群、母題和平行段落等。更重要的是,她引用了當時出版的唯一一本喬伊斯筆記《喬伊斯的笨拙涂鴉》(James Joyce’s Scribbledehobble: The Ur-Workbook for Finnegans Wake, ThomasConnolly ed., 1961),偶爾還援引未出版的筆記。
除辨認字詞,懷特力圖將中文在《守靈夜》中的地位拔高——中國語言文化為解讀這部作品提供鑰匙。漢字符號超出其聲音的特征,符合《守靈夜》聲音/意義的母題,透過該母題,中文和心理分析聯(lián)系起來,如小說所示,“follow my little psychosinology”(psycho心理的+sinology漢學)。漢語音義之二分,提示小說表層與深層意義之二分,由此呈現(xiàn)潛藏或禁忌主題。中國提供的另一把解讀鑰匙是“漢與匈奴”母題。匈奴、蒙古和滿族等游牧民族盡管一度統(tǒng)治中原,卻被漢化,亦即被其對立面同化。因此,漢和匈奴(Han/ Hun)這組二元對立很適合用來象征小說的兄弟—戰(zhàn)爭主題。
懷特研究的主要問題是臆測成分太大,一些推論轉彎過于復雜,難以證實,少數條目因喬伊斯筆記的發(fā)現(xiàn)而得證偽。但她畢竟是系統(tǒng)破譯《守靈夜》中文的第一人(不晚于1967年),而且很可能是研究《守靈夜》的學者中迄今唯一一位漢學家。其大部分推測未被采納,但我們目前所知的《守靈夜》中文知識也主要受惠于她。
喬學者的集思廣益
懷特以大英博物館為據點獨自破解中文時,歐洲大陸有一批年輕熱情的體制外喬學者自發(fā)組織研討。麥克休的學術隨筆《〈守靈夜〉之旅》(The Finnegans Wake Experience, 1981)勾勒了六七十年代他個人的研讀經歷及學界的互動情況。麥克休是英國昆蟲學博士,因癡迷《守靈夜》而定居都柏林。早年他在不依賴二手文獻的情況下攻讀《守靈夜》,偶或參加國際會議,然知音甚少,唯“歐洲《守靈夜》研究小組”的私人聚會是個例外。1970年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學者的家里,約14人討論5行文本,其中與中國有關的一句是:They did oak hay doe fou Chang-li-meng when that man d’airain wasbig top tom saw tip side bum boss pageantifiller。常年為蝗蟲錄音的麥克休承擔了討論錄音的轉寫工作。這段討論很復雜,此處僅概述與中文相關的結論:學者們先懷疑oak hay doe fou這四個單音節(jié)詞來自中文,后認定是英語中的外來語Auto-da-fé的變形,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處置異端者的火刑;Chang-li-meng借漢語讀音,指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殺異教徒者(懷特女士也作此猜測);man d’airain即Mandarin滿大人,中國高級官吏;topside是洋涇浜語,居高位的,應是從中文“上頭”或“上邊”直譯而來;pageantifiller=pagan-killer,殺異教徒者。從這段錄音,我們既可了解中國在包括喬伊斯在內的歐洲人眼中的刻板印象,亦可一窺《守靈夜》的破譯是多么繁瑣且難出成果的工作!
這群學者意識到如此討論成本過高,不久即中止國際聚會;信息時代之前,更有效的交流平臺莫屬民間刊物《守靈夜小通訊》(A Wake Newslitter, Clive Hart and Fritz Senn eds., 1962-84)和《守靈夜傳單》(AFinnegans Wake Circular, Vincent Deane ed., 1985-92;這兩份過刊均已電子化并可從網上免費下載);新世紀以來,比利時安特衛(wèi)普大學的開源電子期刊《喬伊斯發(fā)生學研究》(Genetic Joyce Studies)成為主陣地,并有問題征答版塊,互動更便捷。《守靈夜傳單》所刊什克拉巴內克的《圣帕特里克的夢魘告白》(Peter Skrabanek, “St. Patrick’s Nightmare Confession (483.15-485.07),” 1985)值得我們注意。喬伊斯一封未出版的信說明,小說將愛爾蘭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5世紀他使愛爾蘭皈依天主教)當作日本人,將本土凱爾特族的德魯伊大祭師(arch-druid)當作中國人,二人分別以日式、中式英語爭論(可見,喬伊斯密切關注當時的國際局勢)。什克拉巴內克認為,小說中的undered heaven由under heaven變形而來,是“天下”的直譯,指中國。小說中的mouthspeech allno fingerforce藏有人稱代詞“吾”的雙關——喬伊斯有一條筆記為“five and a mouth = weak and defensive”(五和口=弱、防御),指字形“吾”。什克拉巴內克認為,喬伊斯不得不注意到另一個更復雜的字形“語”。受技術之限,當時印刷版英語論文中的漢字均為手寫體,什克拉巴內克或誤將“語”左邊“言”字中的三橫和一點看作四橫,得出“四”和“口”,認為喬伊斯既用了“五”和“口”,又用了“四”和“口”:fingerforce=finger four,四根手指,但也是五根手指,以此解釋mouthspeechallno fingerforce藏“吾”和“語”字,似可信。作者看起來不太懂東方語言,除了用《漢語與漢日分析字典》(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 Japanese,1923),他還得到兩位日本學者的幫助。也正因此,很多字被看作日語,中文的分量淡化了。無論如何,該文是喬學界東西合作的范例。什克拉巴內克隨后又發(fā)表兩篇文章,分別解釋包括漢語在內的多語種的“和平”“死”這兩個關鍵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引證了不少喬伊斯筆記,這正是70年代末興起的發(fā)生學研究(genetic studies)的重點研究對象。
喬伊斯筆記的秘密
隨著1978年63卷本的巨型叢書《喬伊斯檔案》(James Joyce Archive, Michael Groden, Hans Walter Gabler, DavidHayman, A. Walton Litz, and Danis Rose eds.)的問世,發(fā)生學研究逐漸成為《守靈夜》研究的主要方法論,即追蹤文本如何生成、發(fā)展而至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樣貌。從1923至1939年,喬伊斯花費16年寫作《守靈夜》,不是憑空想象,而是一個嚴謹的累積過程。他生前將草稿、打字稿、校樣和印刷版贈與其贊助人韋弗小姐,后者將之轉贈給大英博物館。此外,1940年喬伊斯一家逃離被納粹占領的巴黎時,家中的許多筆記未做處置,好友萊昂(Paul Léon)將筆記救出,它們后來大部分為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所有。《喬伊斯檔案》以20卷篇幅再現(xiàn)了現(xiàn)存大英博物館的喬伊斯草稿、打字稿等,以16卷篇幅再現(xiàn)了現(xiàn)存布法羅的《守靈夜》影印筆記。

詹姆斯·喬伊斯
筆記尤其藏有解謎的鑰匙,其共計14,000頁,67本,其中49本用于《守靈夜》,余18本未用上。影印筆記本身難以辨認,需學者轉寫、加注。《喬伊斯檔案》問世前,已出版的轉寫筆記有前文提到的《喬伊斯的笨拙涂鴉》及《喬伊斯的索引手稿》(James Joyce’s The Index Manuscript: Finnegans Wake Holograph Workbook VI.B.46,Danis Rose ed., 1978)。其后,則有《布法羅〈守靈夜〉筆記本》系列(The Finnegans Wake Notebooks at Buffalo, Vincent Deane, DanielFerrer, and Geert Lernout eds., 2001-2004),目前已出12冊筆記本,這項龐大的工程還在進行當中。一些零散的轉寫、注釋亦見于《守靈夜小通訊》《守靈夜傳單》和《喬伊斯發(fā)生學研究》等刊。
喬伊斯的筆記對破譯中文有什么用?這要從其讀寫習慣說起,喬伊斯閱讀甚廣,筆記簡潔而恒久,凡某詞寫入小說,他就用不同顏色的蠟筆劃去(盡管少數情況下未嚴格遵守),以保證自己不重復用。晚年他眼疾厲害,請秘書將未劃去的筆記謄到另外的大本子上,這樣繼續(xù)工作。學者通過高清圖片辨認其筆跡,特別是通過不同顏色過濾等技術手段,力圖恢復為彩色蠟筆劃掉的語匯,再根據各方信息追溯該詞可能來自哪本書或哪一期報紙的哪一頁,并給出它在小說及大英博物館手稿中的具體位置。可以想象,這對學者的知識結構要求極高——不僅《守靈夜》須爛熟于心,會多門外語,且常年浸淫于喬伊斯的時代,看他可能看的經典、書報和流行文化。猜測即試錯,可能萬般嘗試而一無所獲,又由于大部分文本乃喬伊斯自編的混成詞(portmanteau words),網絡搜索功能也不能直接幫上忙。筆記注釋工作雖艱辛,其成果卻令人欣慰。國內很難見到喬伊斯的影印筆記,根據西方學者的《喬伊斯檔案》書評,外語詞匯主要集中于VI.B.39、40、46三本筆記。其中,僅46號筆記本已轉寫并出版,即上段提到的羅斯編輯的《喬伊斯的索引手稿》。可喜的是,其中包含中文筆記。
這部分筆記被喬伊斯冠以題名“中文”,實屬難得。據迪恩介紹,喬伊斯一般不給筆記加標簽,它們來源廣泛,記錄隨意,但46號是少有的具有系統(tǒng)性的晚期筆記本,關于中文的發(fā)生學研究或可自此開始。由于這部分筆記復雜且含不少法語詞,羅斯推斷,其來源可能是一本用法語寫的介紹性專著或語法書,而非字典。如圖1所示,左右兩邊為同一頁筆記,只是右邊經電腦處理顯現(xiàn)被劃去的字。第三行第一個詞是被劃掉的syllables;羅斯的注說,漢字絕大部分是單音節(jié),同音字比例高;這條筆記演變成《守靈夜》中的words all in one soluble。筆記寫道,中國人習慣將r發(fā)成l(有誤,中國只有一些南方人才會如此發(fā)音,而愛爾蘭口音確實如此),喬伊斯對這一點特別感興趣,該母題在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從而幫助學者判斷洋涇浜語。除音調、官話,筆記還提到,中國方言雖多,書寫形式卻是唯一,讀音也是確定的。喬伊斯甚至對古漢語的反切注音法感興趣,記下“sujsi fantsie”(圖中第三行后兩個詞),并試圖在另一條筆記“h(en) (m)an”(圖中倒數第五行)中應用反切法,上字取輔音h,下字取元音an。盡管我們不清楚他想要造什么字,這兩條筆記后來也未寫入小說,喬伊斯對漢語的求知欲卻躍然紙上。他明確列出的中文字有:兵、國、魚、王、愛、羊、字等,它們后來都或原樣或裝扮地進入《守靈夜》。下一頁筆記(圖2)集中于當代中國歷史文化:漢口(hankowchuff,羅斯解杭州,誤,漢學家懷特解漢口,對,因小說語境與武昌起義有關)、義和團、磕頭、面子、孫逸仙等,這些也都寫進小說。
同一時期,麥克休在《守靈夜小通訊》上發(fā)表45號筆記本中關于孔子的3頁內容,是迄今可見關于中國的最集中的喬伊斯筆記。這是另一份少有的含標題筆記——題為《孔子》,內容基本來自克勞《孔子的故事》(Carl Crow, Master Kung: The Story of Confucius, 1937),這就大大簡化了編輯的工作,或因此該部分得以單獨發(fā)表,而整體的45號筆記本尚未轉寫出版。麥克休的文章分三欄,分別為筆記內容,對應《守靈夜》的頁碼、行數,以及《孔子的故事》的文摘。克勞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商人、報人,從引文判斷,《孔子的故事》應是從《史記·孔子世家》改編而來,錯誤頗多,突出異域色彩。喬伊斯筆記可分類如下:孔子的生平,包括父母禱于尼山,孔子生于空桑,額上長包(《史記》記載“首上圩頂”,即頭頂凹陷,恰相反),人謂之“長人”(Kung the Tall,克勞或麥克休解為孔子之父,誤),身高,官職,甚至包括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的數量;中國物產有棉、絲、姜、茶壺、熊掌、筷子等;文化方面有禮(propriety, etiquette及上樓之禮)、《中庸》、保存古樂等;社會方面有女性地位卑微、求子心切、苛政猛于虎等;歷史掌故有烽火戲諸侯、二桃殺三士、斗雞之變等;神話傳說有麟吐玉書、“三腿牛”和“大蛇”(《史記》記載有單足牛“怪夔”與“怪龍”);技術方面有中醫(yī)、用于帛書的墨的材料等。
如果說喬伊斯如許多西方人一樣對“中國形象”感興趣,那么特別的是,他也記下很多通常對外國人來說無甚意義的專有名詞,其旨趣更在于聲音與修辭。克勞將曲阜意譯、音譯為Zigzag hill (Chufu),喬伊斯記Chufu Zig Zag hill,在《守靈夜》中成為Zig-zag Hill, zogzag, chuchuffuous,且前兩處語境與中國毫無關系。筆記中的老子、道家Laotze (Taoism),在小說中被改造成一對尾韻laotsey taotsey。喬伊斯關注文言“國”(the Country,類似的,“河”the River)的特指表達,以及其他稱謂如“天下”“中國”,還加上克勞未寫的“the flowery kingdom”(見于喬伊斯常借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1版,或指“華夏”,“華”通“花”),并寫入小說:“We who live under heaven, we of the clovery kingdom, we middlesinspeople”。其中,the clovery kingdom來自筆記the flowery kingdom(華夏),middlesins源自筆記the middle kingdom(中國)。而“孔鯉”“秦”“齊”“魯國”“三桓”這些更生僻的專名表明,喬伊斯的好奇心遠遠超越東方主義式的獵奇。《史記》載孔子學琴的故事,孔子對樂曲理解的四個境界為“曲”“數”“志”“為人”;克勞分別譯為melody、rhythm、mood、the kind of man;喬伊斯的筆記照抄前三項,第四項則寫成manner of man;《守靈夜》作“the melos yields the mode and the mode the manners”。喬伊斯既抓住典故的精髓,又以藝術家的直覺改寫克勞對“為人”的直譯the kind of man,刪rhythm,拆melody,改mood,得一組形式與內容堪稱完美的頭韻melos、mode、mode、manners。而且,克勞將“眼如望羊”誤譯為the calm gaze of a sheep(羊通洋,望羊即遠望),喬伊斯在括號中記下sheep卻未寫進小說。
正是主要基于這篇文稿及《喬伊斯檔案》所錄筆記,美籍華人余定國發(fā)表了國際上屈指可數的與中國相關的《守靈夜》論文(Cordell DK Yee, “Metemsinopsychosis: Confucius and Ireland in Finnegans Wake,” ComparativeLiterature Studies, 1983)。其他已出版的筆記中也偶有中國相關的語匯,我們期待更多轉寫注釋版筆記面世。
喬伊斯曾說,《守靈夜》無一字無來歷。2002年,當今最著名的喬學家、蘇黎世喬伊斯基金會主任森(Fritz Senn)估測,《守靈夜》80%的內容尚不可理解。即便中文版第一部已由戴從容翻譯出版,我們也不能像討論一般作品那樣討論《守靈夜》,將其當作透明的意義載體。《守靈夜》中文破譯之旅是《守靈夜》研究的一個縮影,充滿挑戰(zhàn),偶有驚喜。漢學家的綜合推測為后來者提供了有益參考,發(fā)生學學派的“考古”工程為語義解讀提供了有效線索。既然中文是建構《守靈夜》巴別塔的磚石,中國學者的聲音就將不可或缺,誠如八十年批評史所昭示的,人類要讀懂《守靈夜》,有賴于多方切磋與合作。或許,其意義不止于弄懂一部天書,更在于三百年的忙碌過程本身——《守靈夜》吸引著人們(包括一批昆蟲學、物理、化學等其他專業(yè)背景人士和非博士、教授的體制外研究者)在喬伊斯的引領下攀越人類精神歷程中的一座高峰。
(Vincent Deane答復了筆者的諸多問題并提供寶貴資料,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