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田間來,還回田間去” ——記“擂鼓詩人”田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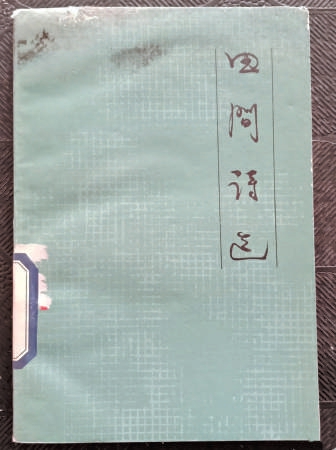
《田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年版
田間(1916-1985),原名童天鑒,現當代著名詩人。幾乎從創作伊始,他就以關注社會變革和人民命運為己任,尤其看重詩歌鼓動群眾、振奮人心的效果。其詩歌文風質樸,語言簡練,卻又寓含無盡力量,形同一篇篇吶喊檄文。誠如斯,他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或曰“擂鼓詩人”。今匯集兩篇文字,或寫其戰斗一生,或釋其詩歌精妙,以饗讀者。
中國新詩的天空,一彎新月,群星燦爛,田間是我所敬重的一位詩人。一本《田間詩選》,我不知翻閱了多少遍。寫于抗戰時期的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街頭詩”,在那烽火連天的抗日年代所起的鼓動性、號召力都是難以想象的。我至今還能背出幾首。
如寫于1938年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如寫于1943年的《堅壁》:
狗強盜,
你要問我么:
“槍、彈藥,埋在哪兒?”
來,我告訴你:
“槍、彈藥,統埋在我的心里!”
這是平樸的描述,這是激昂的呼喊,詩句短小精悍,蘊含深意,且不會因歲月流逝而減弱。
1956年7月1日,田間應邀參加在中南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35周年大會,毛澤東主席與他親切交談。在談到抗戰時期延安的“街頭詩運動”時,毛澤東說,“你們搞的‘街頭詩’運動影響很大,各解放區都寫‘街頭詩’,對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作為抗戰前夕詩壇上崛起的新星、中國新詩的開拓者之一,詩人田間所寫的詩句里,充盈火熱的時代氣息和強烈的愛憎感情。
田間,出生在安徽無為縣羊山腳下,17歲時考入上海光華大學,這所大學的前身為圣約翰大學。文學家趙家壁、小說家穆時英等人均出自此校。入學后,田間即與幾位詩友結為知己,第二年便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文學叢報》《新詩歌》的編輯工作。
“七七事變”后,田間在武漢一氣呵成寫成長詩《給戰斗者》:“……斗爭或者死/我們/必須/拔出敵人的刀刃/從自己底/血管……/不能/屈辱的活著/也不能屈辱的死去……”長詩充滿了火光、鼓聲、怒吼,表達了人民反抗侵略的決心。詩作在《七月》雜志上發表后,即刻震撼當時整個抗戰文壇。胡風贊賞他敏銳的感覺力和奔放的想象力,聞一多稱田間為“擂鼓詩人”“時代的鼓手”。艾青說:“田間很年輕,20歲就出版了《中國牧歌》等詩集,他的詩具有很濃的生活氣息與獨特風格。”
新中國成立后,新的生活召喚著詩人,從解放區根據地走來的田間,在擔任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秘書長、《詩刊》編委、河北省文聯主席等職期間,繼續以其詩風明快、詩行簡短、詩意深長的特點,為這個新時代擂鼓歌唱。印象最深的是讀他的敘事長詩《趕車傳》,這是田間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作品通過貧農石不爛尋找樂園的過程,描繪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斗爭的艱苦歷程。這部詩的藝術特點是,結構靈活,除第一、七部外,其余五部皆以五個人名為題,每一部以一個人物為中心,獨立成章,這樣便于對每個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進行刻畫。句法采用六言和七言三拍的格式,明快嚴謹,朗朗上口。在敘事主人公之外,詩人還塑造了一個抒情主人公,讓他在每部詩中或詠懷,或議論,或譴責,以增強敘事詩的抒情效果。
田間的詩形式多樣,信天游、新格律體、自由體都有嘗試。在新詩的民族化、大眾化方面,他作過一些新的探索,以平樸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喚形成了明快質樸的風格。
“文革”后,田間繼續引吭高歌,出版了《清明》(河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青春中國》(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兩部詩集。只消看一眼書名,就已知曉蘊含其中的深意。
田間說過:“真正的詩人,在琢磨詩歌的同時,是會琢磨自己靈魂的。”他一生都在戰火中淬煉,在戰斗中成長,在時代的造山運動中經受艱巨的考驗,實現靈魂的升華。他那戰鼓般激昂的詩句,永遠留存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1985年,詩人病逝。回顧他這一生,都是憑著一顆質樸之心在生活、工作,正如其詩所寫,“它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在這大地上。”
“我自田間來,還回田間去。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在我家鄉的土地上。”田間終其一生都惦念著他摯愛的人民,把一腔情思寄撒在生養他的這片土地上。他就是這樣一位屬于土地、屬于人民、屬于時代的詩人與擂鼓手。
(作者為舊書收藏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