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筆墨為槍 筑起心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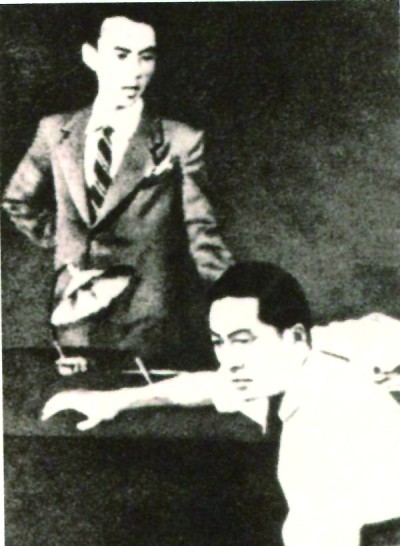
《心防》劇照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39年5月的一天,沉悶的空氣壓在黃浦江上,渾濁的江水看似沉默,但依然洶涌,像極了上海淪陷后的人心。
一艘從香港開來的客輪駛入吳淞口,乘客們或是著急收拾行李,或是到護欄邊遠眺租界的十里洋場。突然,碼頭上搬運物資的日軍對船上的乘客發出咆哮,嘈雜的乘客頓時安靜下來。夏衍也在這艘船上,他皺起眉頭掃視岸邊的建筑。租界雖未淪陷,但已插上偽政府的五色旗。岸邊墻上的日偽宣傳標語闖入視野,夏衍的心情無比沉重。
此行是夏衍在抗戰期間唯一一次秘密潛回上海。七七事變后,夏衍在周恩來同志的安排下,擔任國共統戰報紙《救亡日報》共產黨一方的總編輯,并用這個公開身份在國統區從事統戰工作。上海淪陷后,夏衍帶領報社轉移到廣州。
1938年夏,日軍對廣州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轟炸,成千上萬無辜的市民被炸得血肉飛濺。國民黨方面給《救亡日報》派來的總編輯汪馥泉,竟被轟炸嚇破了膽,逃亡香港,再也沒有回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夏衍等人,他們冒著轟炸走上街頭采寫新聞,報道日寇的暴行。一直堅持到廣州淪陷前的最后一刻,夏衍才率領報社人員徒步轉移到桂林。報社到了桂林后,經費與設備都很缺乏,于是夏衍帶著自己的劇本《一年間》前往香港籌款。在香港,夏衍收到從桂林轉來的電報,得知遠在上海的大女兒沈寧病重。原來,夏衍南下廣州前夕,妻子蔡淑馨剛誕下一個男嬰,無法隨遷。他只能留下妻子拉扯一兒一女在租界艱難生活。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收到消息,顧不得多想,夏衍就開始了此番秘密回滬之行。
處理完家事,夏衍著急了解上海淪陷后文化界的情況,于是在一家咖啡館秘密約見了老友、著名記者惲逸群。上海淪陷后,雖然被稱為“孤島”的租界還保持名義上的中立,但日偽勢力向租界當局施壓,所有中國人出版的報紙都要接受日本人的新聞檢查。只有美國商人名下的報紙受影響較小,能夠正常出版。惲逸群放棄撤離的機會,選擇留守孤島。他利用和美商報紙的友好關系,不但自己同時在多家報社發表大量時評,而且組織進步記者為這些報社供稿。惲逸群所寫的評論全是動員抗日和批判投降的檄文,他發表了全國最早揭批汪精衛漢奸言論的時評。當時汪精衛尚未公開投敵。惲逸群的評論引起日偽、國民黨兩股勢力的忌恨,他隨時都有可能慘遭毒手。當時,即便是租界內的報人,只要敢支持抗日,就很有可能遭到日寇和漢奸的報復:多家報館被炸;數十位報人遭到日偽特務暗殺或綁架。就在此前不久,公開叛國的汪精衛在日本特務的護送下回到上海,日寇加緊了對孤島抗日文化力量的絞殺,惲逸群的處境更加危險了。在與夏衍的交談中,惲逸群平靜地講述了這一年多來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他所知道的情況。
聽完惲逸群的講述,夏衍突然想起一年半之前上海淪陷那一天,《救亡日報》社宣布撤往廣州,大家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場景。雖是別離時刻,但這群書生抗日報國的熱情高漲。這時有同志提出要留下,在這孤島里以筆作戰,有人高喊道:“上海淪陷了,但是人心不死,我們一定要筑起一條精神上的防線!”從接頭的咖啡館出來,夏衍走在孤島的街市上,報社同人的那句“人心不死”的呼喊一直回蕩在他的心頭。雖已記不起這位同志的名字,但夏衍眼含熱淚,他再也無法抑制對他們的感佩與對他們處境的憂慮。途經一處報攤,夏衍從報紙上看到,“五九”國恥紀念日這天,有店鋪掛出國旗卻遭到租界當局干涉,這引起商人群體的憤怒,他們以罷市相抗議,最終取得勝利。這時,夏衍才感到有些欣慰:孤島的人心真的沒有死。而這“爛鐵打成鋼”的人心,以及普通民眾秉持的抗戰必勝的信念,這里就有惲逸群等報人的功勞。
從孤島回到桂林,一個以惲逸群等孤島文化界抗日力量為原型的劇本在夏衍心中有了雛形。起初,夏衍想在完成《愁城記》之后再寫這部劇。然而1940年春,汪精衛在南京宣布成立偽政府,這時他覺得這部話劇的創作已經刻不容緩。他很快寫好劇本,定名為《心防》。
《心防》的主人公劉浩如既是報人又是劇人,領導孤島文化界的抗日救亡運動。這一人物以惲逸群為原型,又雜取了于伶、梅益等同樣在孤島堅守的文化戰士的經歷。劇中的劉浩如無私無畏,巧妙地與日寇漢奸周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最后卻被漢奸打黑槍殺害于劇場。倒在血泊中,他依然不忘詢問身邊的同志:“咱們的防線沒有失守嗎?”《心防》在桂林、重慶、昆明等后方大城市的多個劇場上演,并被各地的演劇隊不斷在城鄉之間巡回演出。
除了《心防》,夏衍在抗戰期間寫作的《一年間》《愁城記》《水鄉吟》《離離草》《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等話劇,無一不是鼓舞抗戰士氣的杰作。夏衍以筆墨為槍彈,在無數觀眾讀者心目中筑起了一道道“心防”。
(作者:朱超亞,系蘭州大學文學院研究員)


